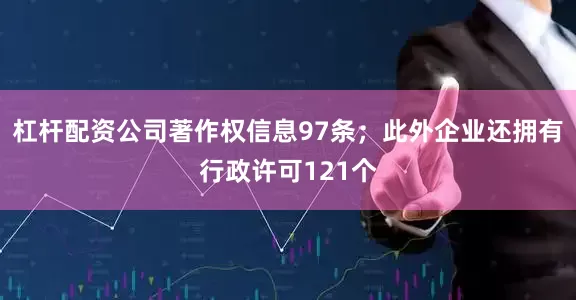前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就1970年庐山会议的经过与结果,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与剖析。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1970年至1971年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篡夺最高权力,并密谋发动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展现出了非凡的机智,成功挫败了这场叛乱”,“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对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记忆所及,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吴德,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1970年之前,我始终处于一种被暗中怀疑为叛徒的状态,接受着审查。尽管这种审查是背对背进行的,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某些事情似乎并不寻常,总有一股别扭的感觉。例如,我未能受邀参加市里的某些会议,而对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我也未被告知。
尽管当时我尚不知晓具体缘由,然而在那个年代,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对一切进行颠覆,党的生活显得极不寻常。我一方面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保持从容不迫,坚信党和人民终将分辨出是非曲直。
1970年8月,恰值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在即,我忽然接到一项通知,要求我带领北京市的中委与候补中委一同前往庐山参会。这份看似寻常的通告,却意外地让我感到惊喜,不禁松了一口气,内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激动。
我忆起,同行者包括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抵庐山,气氛并未显得紧张,我万万未曾料想到,一场浩大的风波即将降临。
大会的编组工作是以六个主要区域为基准进行混合编排的。其中,华北组的负责人由李雪峰担任,而我则担任副组长一职。其他副组长分别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以及军队的郑维山。此外,华北组还包括了陈伯达、汪东兴等成员。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涵盖两项内容:审议宪法修订案以及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在会议前夕,毛主席又提出了关于当前形势的讨论议题。会议闭幕之际,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有关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对宪法进行修订,中央特地组建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担任委员会的主任,林彪则出任副主任。该委员会之下设有专门的小组,成员包括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均为政治局成员及军委办事组的骨干。
宪法的一次关键修订涉及对国家体制的调整,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此建议最初由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此后毛主席亦多次提及此事,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我铭记于心的是两次重要的情形。第一次,是汪东兴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即国家主席一职将不设,毛主席本人亦将不担任此职,遗憾的是具体的时间节点我已无法回忆。第二次,则是在林彪提出建议恢复国家主席职位,并建议毛主席出任此职之后,毛主席作出了批示,明确指出“此议不妥”。值得注意的是,汪东兴传达该指示的时间点是在林彪坚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前夕。
8月23日的午后三点整,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拉开帷幕,随后,林彪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林彪,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及副统帅,更是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我那时以为林彪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均系中央意志的体现,并未察觉其中有何特别之处。然而,8月24日的上午,政治局传来通知,要求我们聆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反复播放了两遍。
8月24日的午后,华北小组召开了首次会议,议题集中在林彪的讲话内容上。遗憾的是,我并未参与此次会议。据我所知,林彪办公室曾通知要求各省、市各自整理一套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材料,北京市亦在此列。
鉴于时间紧迫,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送达,加之我对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便提议由数人共同协作,整理一份材料。于是,我与黄作珍,以及随我们一起前往庐山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便开始共同着手整理这份材料。
8月24日的午后,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急切地率先开口,表示:“在宪法中明确确立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以及最高统帅的地位,意义重大,这一地位的确认历经诸多斗争与考验。”
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亦相继发言,其核心观点在于主张由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并提及了部分人士对毛主席担任此职的异议。随后,陈伯达发表讲话,听众中仍存有疑虑。然而,当汪东兴发声后,情况便截然不同。毕竟,他是毛主席的亲信,因此众人更倾向于信赖他的言论。
会议结束后,吴忠向我透露了发言的细节,他提及陈伯达与汪东兴均发表了讲话,并指出有反对毛主席的声音。我紧迫地追问,究竟是谁对毛主席有所反对。吴忠回应道,他们并未直接点明姓名,因此无从得知具体是谁。此时,会场内外已开始热议此事。
夜幕降临,我与李雪峰在会场偶遇了汪东兴。我向汪东兴探询:“究竟是谁反对毛主席?”他回答道:“是有这样的人。他们要么掌握着枪杆子,要么操控着笔杆子。”转而询问李雪峰,他却表示自己也不得而知。我对此愈发困惑,不知这究竟指的是哪一类人。
夜幕低垂,时针指向了11点之余,我与李雪峰、解学恭共进晚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身处华北组的简报小组,积极参与了简报的汇编工作。她将精心整理完成的简报稿件呈上,等待审阅。该简报的核心内容,正是陈伯达与汪东兴的讲话要点。
“关于简报的印发,只需你们两人签字即可,无需我亲自落款。”李雪峰回应道:“简报的编撰秉持着‘有文必录’的原则,签字确认是常规流程,还请您签上您的名字。”
于是,我在即将付印的简报稿上留下了“吴”字的签名。我们在完成签字手续之后,该简报随即被送往中央办公厅。经过迅速的印制,很快便发放出去。这份简报是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同时也是全会的第六号简报。8月25日清晨,华北组的会议得以继续召开。
一夜之间,舆论的焦点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所谓有人对毛主席表示反对的话题。部队的同志们发言时情绪激动,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即便是陈毅同志,也表达出坚定的立场,他表示,无论身处何地,哪怕有人在隐蔽的角落里反对毛主席,他陈毅也必定将其揪出。

聂元梓
彼时,北京团队的聂元梓再度彰显了“造反派”的势头,异常活跃,四处联络串联。她联络了河北的同志,以及军队后勤部门的同仁,直至与吴忠取得联系。她对吴忠透露,有人暗中反对毛主席,力主揪出这些反对者。
吴忠询问,究竟是谁对毛主席表示了反对,而聂元梓却并未透露具体姓名。吴忠对聂元梓保持着警惕,坦言自己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亦不清楚究竟是谁起了反对之心,因而对深入探讨此问题表现出了拒绝。随后,吴忠将这一情况转告于我,并表示聂元梓正在进行串联活动。
此刻,几位从工人队伍中挑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向我提出,既然其他人已经发表了意见,他们也希望能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回应这些同志道:你们打算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呢?如果问题关乎中央的领导人,依据党的规定,理应首先向毛主席汇报,而毛主席此刻正位于庐山。
此刻,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于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表见解,四处煽风点火,现场气氛颇为紧张。同时,我还留意到王洪文及上海组的人员四处打探消息。

8月25日,我向周总理亲笔致信,信件内容系我与陈一夫同志共同商议后,由他执笔起草而成。信中主要反映了聂元梓同志在各地频繁串联,企图揪出所谓的反对毛主席之人,导致会议氛围变得异常。在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后,我还就后续会议的召开方式征求了他的指导意见。
25日午后,华北组的会议照常召开。李雪峰接到紧急通知,需前往毛主席处参加会议,因此华北组的议程转由我接手主持。河北省的四位由劳动模范脱颖而出的候补中委相继发言,针对新宪法未设国家主席一职的问题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存在瑕疵,并明确提及了康生的名字。这些发言者的观点出奇地统一。
不久后,李雪峰返程。他告知我,会议即刻暂停。我追询暂停的原因,李雪峰回应这是中央的决策,具体细节稍后详述。李雪峰即刻宣布了会议的终止。在离场途中,我再次向李雪峰探询究竟发生了何事,致使会议不得不中断。
李雪峰提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期间对天才问题及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进行了批评。随后,毛主席提议,中央全会分组会议应立即暂停。
李雪峰,我向您指出:“毛主席曾明确表示过不设立国家主席的观点,并提前有过说明。为何在河北,还有四位同志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提出异议?他们甚至公开指摘宪法起草委员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指出:“此次系中央全会,各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如有任何见解,皆可畅所欲言。”
8月25日晚,我正沉浸在电影的氛围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传唤,要求进行谈话。周总理告诉我:“你的信件已经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了传阅。”随后,他指示我返回后,应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召开一次会议,对聂元梓进行批评,并解决她串联活动的问题。我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在会议上对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批评意见。
周总理曾言:“或许涉及到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议题,在纪念列宁百年诞辰的社论中,毛主席曾将其删去。我已指示北京查阅相关档案。关于此事,你为何不在会议现场对他们提出质疑?”
我不了解情况,不便评论。
周总理指出:“这不很明显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毛主席,副手是林彪。你们若是对起草委员会有所异议,岂不是在质疑毛主席的决定?为何不直接表达?”周总理对我进行了批评。随后,我向周总理询问小组会议如何继续进行,周总理回应,按照既定计划继续进行。
自与周总理会面归来,我即刻主持了针对聂元梓非组织活动的批评会议。在会上,我们深入剖析了聂元梓的行为。随后,我们将会议的讨论内容手写整理成一份情况简报,并呈送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对此批示,要求政治局全体成员传阅。我仍记得,林彪在简报上画下了圈圈。然而,随着林彪问题的浮现,我才深刻意识到,我们当时所撰写的这份简报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此刻,传闻中反对毛主席之言论出自张春桥之口,矛头亦指向江青、康生等人。小组会议结束后,政治局随即作出决议,要求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进行反省,并决定撤销6号简报。
在召开检讨会议之际,周总理与康生同志担任了主持工作,各小组组长悉数出席。尽管我并非组长之列,周总理却特意通知我,需旁听他们的自我批评。陈伯达同志率先进行了检讨,随后吴法宪、李作鹏等同志也依次进行了自我反省。然而,陈伯达等人的检讨显得颇为不甚得体。
汪东兴曾与我及李雪峰进行了一次会谈。他透露,这是应毛主席的指示,对他本人以及华北组的几位组长进行的一次交流。汪东兴提到,毛主席曾表达过不设立国家主席以及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而这正是他本人传达的信息。然而,在此次会议上,他却提出了与毛主席意见相悖的看法。
汪东兴曾在华北组进行过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他在发言中所述内容与陈伯达的观点有所差异,那是因为在听到陈伯达提及有人对毛主席提出反对意见后,他一时情绪激动,言辞过激,结果被他人所利用。经过后续的调查,并未发现汪东兴与林彪集团有任何关联。
毛主席始终对汪东兴给予庇护,汪东兴返回北京后,在机关进行了几次检讨之后便不再继续。8月31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批判。自此,关于宪法的问题不再被讨论,计划问题亦然,众人纷纷转向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9月6日,第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幕。
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重点阐述了加强干部路线教育、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周总理及康生亦相继发言。周总理主要负责部署批陈整风的具体工作,而康生则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对陈伯达进行了审查的公告正式发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同时亦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强化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毛主席自外地归来,抵达北京。我接到通知,需与纪登奎、陈先瑞、吴忠一同前往丰台车站,等候与毛主席的会面及交谈。抵达丰台车站时,毛主席的专列早已抵达,他在列车上与我们进行了谈话,汪东兴亦在场。
其一是强调共产党应坚持唯物主义,摒弃唯心主义的诱惑;其二则是将陈伯达比喻为“船上的老鼠”,意在指出其见风使舵,当发现一艘船即将沉没时,便急忙跳到了另一艘船上。
毛主席的言辞,让我顿悟到陈伯达背后,隐匿着更为显赫的存在,不仅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更是一位地位更为尊崇的人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转向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回想起谈话的结束时刻,陈先瑞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持续乘坐火车返回北京,而我等则搭乘汽车返程。
归庐山之行已多日,周总理便将我召见。他将我致他的信件与那份针对聂元梓的批评简报交至我手,命我予以销毁。我返京后立即将这两份材料妥善处理。此时,我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周总理的考虑果然周全。
1970年12月召开华北会议召开华北会议,凸显了问题的严峻程度。这次会议似乎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三人负责主持。在会议召开前夕,周总理与我们数人进行了深入谈话。他首先阐述了毛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具体批示,接着指示我、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进行自我检讨,并对陈伯达进行揭批。
在会议中,我们数人共同对华北组在庐山期间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具体包括两点:一是对6号简报的处理,二是盲目附和陈伯达的行为。吴忠等同仁亦在华北会议上对自身在庐山期间的不当表态等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华北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江青在会上点名批评李雪峰,指责他擅自将河北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的行为是一场阴谋。
李雪峰就任河北省委书记及省革委会主任之际,陈伯达亦随同前往。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对中共冀东党组织进行诬陷的演讲,导致众多人遭受迫害,甚至有人因此丧命,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冤案。陈伯达的问题进而牵连到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倍感焦虑,遂派遣其秘书返回石家庄,焚烧所有相关文件与档案。
李雪峰派遣秘书返回的消息,不知为何被人窃得。秘书尚未有机会销毁文件与档案,便被紧随其后的来者悉数没收,同时,李雪峰的住所亦遭到了抄家的命运。事态愈发严重。周总理指示我们协助李雪峰,我于是前往京西宾馆探望了他,这次拜访成为了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后一次见到李雪峰的机会。
在华北会议期间,有关李雪峰与陈伯达之间关系的说法被提出。然而,根据彼时的具体情况,我坚信李雪峰与陈伯达并无特殊瓜葛。他在北京市的任职时间不过短短七十日,而对于他的思想状况,我有所了解。此外,他同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某些问题上存有明显的分歧与对立情绪。
李雪峰不久后遭解职,并被下放到安徽的农场劳动,其后更被开除党籍,遭受了极大的打击。郑维山亦同样被剥夺了职务。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有幸在一处招待所中与李雪峰重逢。随后,他的党籍得以恢复,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委员,并最终成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在华北会议的筹备阶段,我主要反思了自身因受陈伯达言论影响而做出错误判断,以及在6号简报上签署姓名的失误。鉴于我未能参与8月24日的小组会议,并在8月25日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因此未能进一步深入检讨更多问题。
不久后,我在翻阅李雪峰家中搜集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他所撰写的庐山会议日志。在日志中,他详细记录了8月25日我与他在河北同几位同志进行发言时产生的分歧。纪登奎在得知我找到了李雪峰的日志后,向我传达了中央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与陈伯达、李雪峰等人并无瓜葛,亦未曾参与8月24日的小组会议。
于是,周总理与我进行了交谈。他对我未参加那次会议却擅自签署简报表示了批评,并要求我在大会上进行发言,对陈伯达进行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免除了我进一步的检讨。我对周总理坦言,我对陈伯达的具体问题了解不深,只能依照中共中央即将发布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来进行批判,并在发言中对我个人的失误进行反思。
配资交易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官方炒股软件始终是守护毛主席的安全
- 下一篇:河南股指配资活脱脱把争执变成了个人秀场